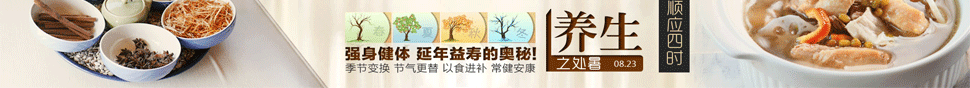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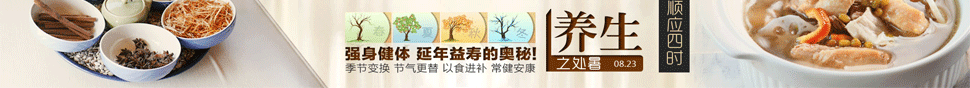
怀念外祖父和他的庄园
作者:金玺东
我们大多数人,一生中和父母生活的时间不过十多年,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,和外祖父母相处的时间就更加珍贵了。
高铁就要启动,我在三天前收到消息说外公过世了,此刻我坐在回老家的车上。也许是因为心灵感应,此前好几天里我都有无法抑制的心神不宁,我思忖着外公很难迈过去这一关。在视频里看到他咳不出来的难受,以及“啊哟啊哟”的呻吟,我知道那一声声都牵动着亲人们的神经。
在我的内心,我无数次怀念过外公的“庄园”。搜寻我童年时留下的记忆碎片,只有在外公家的那些时光最具画面感。
30年多前,外公50出头,我是他的第一个孙儿辈。我妈妈是老大,我的姨们和舅在我出生后好几年,才开始各自成家,所以我顺理成章地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每次到外公家,他会用下巴下的硬茬来刺我;我调皮捣蛋的时候,他会用弓着的手指来敲我,一敲惊魂、再敲轰隆的那种真敲。直到后来,他已经不能轻易抱起我坐到他的膝盖上,敲头的手也不会再举起。高铁向前驰骋着,忽明忽暗的光线里,记忆中的一幕幕向我展开……
(一)记忆中的庄园
外公的家傍在一个山坡上,山呈左右延伸,形成一个7字的小窝,这使这座我童年的庄园既不与其他人家咫尺相接,又不显得遗世独立,相对于那种大湾大屯,这里少了随时的走邻串舍和避之不及的家里长短。从家里向远处看,隔着一里远的农田可以看到一条大马路,三十年前传来的全是拖拉机和三轮车哒哒哒的马达声,拖拉机冒着黑烟,三轮车的前轮隔远看只有盐坛子盖那么大。幼小的我,感觉这里要比我家发达多了。
外公的楼房大约建于89年,那时候还非常多人住土砖房甚至茅屋。我已经不太记得建房前的老房子了,但是我对开建楼房的时间点有一些印象。在小孩子眼里,新楼房好像很快就建完了,房间多了很多,之前的老房子里拴过打猎抓回来的野鸡,但是新房子建好后就没有关过野鸡野兔斑鸠这些了。现在的小孩子没见过鸟铳,这种登顶中国民间杀伤力排行榜的武器,外公家就有三枝,他们村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洋枪队。
跟着我的视角,你可以了解一下庄园的各个方位。
那是一栋红砖高瓴的楼房,有一个宽阔的前坪,右边是相连的杂屋,左边是果园。果园和前坪用花窗格子砌成的围墙界开,这样,前坪开阔,果园井然,围墙上还放着诸如兰花仙人掌四季果之类的盆栽,还有一味刀伤药。刚开始果园最多的是桔树,边边角角上种着各种叫不上名的药材,昭示着主人懂不少的草药知识。跌打损伤或者被毒蛇咬伤,在这里都能找到对症的草药。到后来有一年大雪冻死不少桔树后,其中一块改种了天麻,天麻花开,有自家的蜜蜂忙不迭地落到花上,在微风中摇曳。这些蜜蜂飞自屋后的几个蜂箱,常年产蜜,到现在都没有间断过。外公亲自培育的金钱桔,是由枳壳嫁接而成,丰收的年轮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。还有一棵高大的芭蕉和零星的百合。其实还有更多的种植物,已经不能一一列举,一切都像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一样充满感情。
后山也有不同品种的桔树,以及为数不多的猕猴桃藤和蜜桃树。往山上走,有一大半是茶树,间杂着苗条的山胡椒树,左边一小半则栽有板栗树。这块茶山,那时候供应了我们常年的用茶量,直到后来杉树长大成材遮蔽了阳光,茶树才退出历史舞台,山胡椒树也渐渐消失。我依然可以记得采茶的季节,成篓成篓的嫩叶倒在地上的那种忙碌。
再回到屋前,楼房右边的杂屋的尽头有一两枝枇杷树,还有爬上杂屋顶的葡萄藤。再前一点是一棵并生的老杨梅树,一树直立,一树横卧。端午时节,熟了的杨梅,又甜又不可避免的酸。每年都有一次集中的采摘,至少也有好几十斤。外婆会留下来过节时一起吃。杨梅树下是一口池塘,歪脖子的那一半树,几乎把整个果枝都探在水面上,一两个成人站上去也不一定能晃得动。以至于每次打杨梅的时候,要在水面上放一个盘箕,让杨梅落入盘内,打完一边再打另一边。有一年我看杨梅噼里啪啦地掉入盘内,就得意地叫“打杨梅了,好多的杨梅”,结果被哪个姨瞪了一眼——80年代物资匮乏,人们看到什么东西都会眼红,你可以细品……
外公外婆常年都会酿米酒,用的是外公自制的酒曲,家中总有一大缸的库存,有几次我就喝着甜酒睡着了。米酒可拿来泡药材,也可以泡杨梅。甜甜的杨梅酒比起现在的青梅酒,更具实质。澄亮的大玻璃瓶里,占去一半高度的杨梅,或黑或红或白,沉淀出枣红色的诱惑。
不管是自家泡制的药酒,还是别人送他的好酒,上门的左邻右舍只要小坐一会,外公就必会倒上一杯。好酒!客人边喝边赞着,外公始终笑盈盈的陪着。
前坪的下方是一个菜园,菜蔬井然,繁茂翠嫩不用多讲。但是相对于我家田地少,有一个正经的菜园突出它的难得了。田地不足的地方,分田到户的前十年,普通人家的那点地都不够吃饭用,要留出来种菜那是不可能的,我家就是在山边或者田埂上种几根菜苗,谓之菜地。外公家不同,除了有白米饭,我还吃过红米饭,还有红薯,还有大量的红薯粑粑(片)吃。我们家是“正经”人家,是田就不能用来种菜,是地就不可能用来种红薯。
菜园和池塘的角上还有一棵石榴树,一年又一年,看着石榴树不长年轮,但是每年必结果实,不是那么粒大饱满,但是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果树挂果,这种喜悦也是很不错的!况且石榴树上还爬有鹅黄色的金银花,早就被夏天的凉茶盯上了。
杨梅树的对面,池塘的外沿种着一路的美人蕉,还有一种叫不上名来的颜色鲜艳但不能近闻的花,一丛一丛的,在秋天不是一般的绚烂。把美人蕉的花拔下来,从花管的根部吮吸一下,沁甜的花蜜就会流入口中。有时候我的孩童天性过于释放,一不小心就把所有的花枝都折完了,外婆就会絮絮叨叨个没停。谁叫家里就我一个小屁孩呢,指定就是我折的,没得逃!除此之外,间隔几步就有一棵木槿树,桃红、粉紫或者纯白的花朵,透着朴素淡雅,花多的时候摘下来够做一盘菜吃。还有我非常不爱吃的椿枝。
(二)外公和我
我小一点的时候,跟姨们去山后挖过红薯,也跟舅舅去山后的冷水田里挖过茨菇,就是那种小号的荸荠。还有舅舅会砍回来甜杆儿吃,相当于小号的甘蔗吧。有时候我跟着外公下田,回来的路上有人问起,背着木犁的他,会停下来告诉人家这是他外孙,然后别人就惊讶地说道有这么大的外孙了。再大一点的时候,我帮外公放过牛。
还不懂事的时候,外公会带我去看露天电影,或者到别人家去看电视剧,都是睡得迷迷糊糊被背回家的。外公家什么时候置办的电视机,没有印象了,只知道外公爱看射雕这类武打片。外公爱看书,他所有的知识都是书上得来的,涉及到中药、针灸、风水。想想外公早年还给我看《侠客行》《天龙八部》之类,才知道那时的时光清浅!
我家离外公家大约15里路,走路至少需要1个小时。我爸妈时不时把我往外公家送,偶尔感冒发烧,厌食,更会往外公家送。农忙季节忙,也往外公家送。逢年过节,如果我想留在外公家,我爸妈也乐得让我留下来。外公家的楼房当西晒,下午到晚上都很热,可是我喜欢,毫无疑问这里是我的乐园。听我妈说,我一到外公家就长胖,一回家就开始掉肉。外公调制的疳积药伴着猪肝蒸着吃,我吃了无数次。我小时候无缘无故总是头疼,外公弄的蜜麻花根炖斑鸠或者脑花,我也不记得吃了多少次。
外公身上既有着文化人的温润如玉,又有着技工男的知识技能。就是我妈也觉得外公懂很多。有重大活动时,我们家必然有请,我奶奶见到亲家必然高兴地喊着“外公外公”,外公也是一脸的谜之微笑,对他的大外孙则是一脸的宠溺。外公的微笑,不是那种拘谨的应答式的微笑,也不是那种掌控全局富有感染力的微笑,而是一种内心真正的感到愉快,反过来又能温暖他人的微笑。我们家上了规模的生日庆祝以及嫁娶,外公必然人礼俱到,好久不见外公的我会格外的欢喜,心中就像装着一只撒欢的小羊。只是每次来他总住不了两天,真不想他走,可是我们也留不住他。我记得我10岁生日时,他也一本正经地来赴宴,母亲拿出我的作文本给他看。他认真地看着,没有直接给我什么指导,可是我喜欢他身上那种独特的气质,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叫书卷气。
(三)外公的博闻强识
外公什么都自学成才,他懂的中草药知识维护着一大家子的身体健康,他自己却有冬天必犯的季节性咳嗽,每一声闷闷的,每一声都像没咳完。在打着白霜的冬天早上,除了可以听到村口大喇叭里的广播,我一起床就可以听见他的寒咳声。
虽然外公出道是无师自通,很多人还是会过来找他医治。很少人听说过疳积,这种病以前却很常见,是外公钻研书籍,掌握了针灸和食疗结合的治疗方法。在此之前,他的两个孩子死于疳积就是因为他付不起药钱,但是他掌握了治疗方法后却怜悯他人,治病救人不计收入。听外婆讲,三个鸡蛋都可以抵药钱。外公去世后,出殡的那天早上我亲眼看到沿途的乡亲们为他送行,大卷的鞭炮不在少数。
外公除了懂得中草药,还是当地的“地仙”。别人家要建新房,或者老人故去需要起坟,都会来请他看,而他会穿戴整齐地出发,帆布包或者皮包里装着罗盘。外公不是那种明码标价的人,但他为别人看地必定考虑周全。有的人家还会派车来接他。外公穿着刷过的皮鞋出门,回来的时候带着糖果给孙儿吃。
看地是他的一份职业,我不信风水,但是外公之于我,始终是一种比之别人更自觉敬重的存在。
(四)鲜为人知的黑暗岁月
外公受过的苦鲜为人知。投胎是个技术活,可是外公在错误的时间出生在土豪家庭,这注定他要度过人生一段中最黑暗的岁月。
阶级成分不好,这顶帽子就像一座前世降下的大山压在他身上。别人家可能没柴烧没米吃,可是外公家连猪草都没得地方扯,因为阶级成分不好一点点小事都可以无限扩大,他怕受批评和斗争。一家老小的生存问题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,阶级斗争的铜墙铁壁又让他处处受限。他只能白天黑夜地干活挣工分,落下腿脚疼痛的毛病;好耕的田他挨不上边,他只能去找边边角角那些别人不要的田去耕作;他需要负担病病殃殃四位大人,也需要面对嗷嗷待哺的孩子,处处需要钱,可是在封建父权社会的家庭里,他的父亲紧握着经济大权,连孩子要病死了都不愿意拿出来用,他要面对一种怎样的悲哀?
可以想象,他的内心处在多重的煎熬中,要战胜各样的烦躁,这些经历也让他养成了小心翼翼、隐忍负重的性格,打脱牙齿也和血吞。忍社会之歧视,负一家之重担,直到后来能拨云见月。
但是他对待子女一视同仁,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。常常叮嘱子女不要斗气,不要争吵,与人为善,笑脸待人。和气盈盈的外公的脸上,你仿佛看不到他的皱纹。
(五)依然流年不利
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远去,但贫穷的日子还没到头。做啥啥不顺,按下葫芦起来瓢,外公虽然受了很多的累,但是得不到期望的结果。住的是破旧的茅屋土房,四面墙壁五面透风,屋顶越修越漏雨。外婆说起下雨天,戴斗笠煮饭是常事。更悲催的是,白蚁也趁人之危,房子的门框、横梁都被蛀空,床铺、书桌、壁柜也没落下,床都塌了,窘迫到睡觉只能睡在砖头堆上。可以说是饱尝人世之冷暖,尽历家道之时艰。
在房子随时都有倒塌危险的情况下,外公没有办法,决定新建房子。接下来遇到各种困难,请人做红砖没有钱,装好砖窑后师傅却又没烧燃,绝望之下,他自己想办法把窑重新点起,这时候大雪又纷飞。好不容易把砖烧完,发现火候不够砖不堪用,以至于后来的红砖楼房,部分地方只能以土砖凑数。房子终于落成,可是工钱和预制板钱还没有着落,外公跟人家说,现在实在拿不出钱,但是喂了猪每一次出栏都会主动还钱,绝不会让你们上门催账。那时候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了,我的姨们每天都出去扯猪草喂猪,送了多少头猪,才把欠下的账还清。我印象中,姨们铡过小山一样高的猪草,大锅一滚厨房里全飘着猪草味。
向来萧瑟处,渐立向荣家。外公经受住了严峻的挑战,初具雏形的庄园慢慢地丰韵起来。
(六)离去前的恋恋不舍
外公在生命最后的五年里,医院,医院,医院多呆一两天,好好治疗,多养一养。但最后一次时,可能明显感到情况不对,他没住两天就坚持要回家。在子女们每天伺候左右的空隙里,他跟在外工作的孙儿孙女们视频,手机前的他用手摩挲着我们的脸颊,或者嘬着嘴去亲吻我们的头像……时光不可倒流,如今只剩唏嘘!
外公去世后,除了孙儿孙女,所有的外孙都从外地悉数赶回,恭恭敬敬地披麻戴孝。
(七)感念在心
在回来的高铁上,我寻思着,每一个生命的终点如同一班高铁,上车的人和送行的人再不舍也必然分开,闸门一关,即天人永隔,送行的人怆然止步,坐车的人断然离去。先人之慈爱,亲者之依恋,唯近者知!
水有源头木有根,前人有德后人荫。外公就是我们源头上的一处活水,带给我们的是甘甜,不是寡淡;是清冽,不是混浊;是丰富,不是亏缺;是激励,不是羁绊。外公的善良,不因人生际遇而变易,是始终蕴藏在内心的一种温暖。今天我们常说,善良要有锋芒,可是信心不足的人们往往会过于强调锋芒。
如果说“人之初,性本恶”的信念所发出的爱,是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一种妥协和争取,那么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的信念下爱在人先的行为,就是人际间的一种启导和自信。在外公的微笑里,我们看不到一丝人生的纠结,所有的挫折坎坷没能在他脸上留下一丝痕迹,就是在他的生活中,我们也看不到他叹气、抱怨、灰心的瞬间。他是怎样平复自己的内心,又积极地面对问题并从困境中走出来,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
回顾外公的一生,我们才可以发现他那种向上的力量和默默无声的奋斗。他那种温韧的性格所发出的力量,是我们心底的一束光芒。“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”,外公的庄园早已改变,但是这座庄园所代表的坚韧不拔、自立自强,已成为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
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,人的一生,各种经历,各种关系,各种感情,缠绕在一起,相互交织,犹如包浆一样层层覆盖。有人会缠裹在原来的感情里,也有人从过去的情怀中逃逸,但是所有有爱的故事充满着美好和珍贵,有爱的人永远垂范,值得永远纪念。
作者简介
金玺东,宁乡灰汤人,初爱文学,后学翻译,而从贸易,又染实业。爱文字而止乎此,以为技而不为其囿。常为俗务劳形,唯偶尔玩味也。


